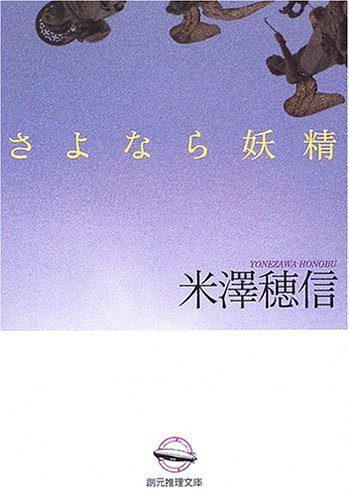视频版: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t4y127rF
故事梗概
故事以倒敘的方式開場:已經升上大學的男生「守屋路行」拜託外號為「船老大」的高中女同學「太刀洗萬智」協助自己,一同找出一年多前隨著父親來到日本的外國人「瑪婭」目前的踪跡。而太刀洗則拒絕幫助他,守屋便只好與高中同學「白河」,通過當年同班同學「文原竹彥」整理好的資料,開始了他們的調查推理之路。 一年多前,守屋跟太刀洗在放學回家的途中看見了來自南斯拉夫的瑪婭。瑪婭的爸爸在大阪工作,而瑪婭原先要投靠的友人卻已因病去世。看著無家可歸的瑪婭,守屋決定幫她牽線,讓她到開旅館的白河家借住。瑪婭認為在日本看到的每件事都有某種哲學(此哲學非彼哲♂學),都值得記錄下來;也因為文化的差異,讓她時常陷入誤解。好比看到雨天有人拿著傘卻不撐就認定日本人都不愛打傘,確沒想到只是單純因為雨傘壞掉要拿去丟掉的而已。 瑪婭、白河跟太刀洗去看守屋跟文原的射箭比賽。瑪婭不懂為何第一場射擊時,守屋命中卻被老師罵,而沒有中標的學生卻得到了老師的稱讚。守屋解釋,命中但姿勢不正確,老師會罵,而姿勢正確老師就會稱讚。日後,一群人前往商店街和寺廟觀光,守屋跟瑪婭和其他三人走散,守屋便帶瑪婭去吃午餐,也買了個繡球花髮夾送她。瑪婭得知紅白兩色是吉祥的顏色,卻怎麼也想不透為何之後拜訪的墳上會擺著紅白兩色的豆沙包。而實際上,紅白兩色的豆沙包只是某人為了激怒遺族而放上的供品。之後瑪婭看見兩個青年人特地準備好麻糬,嘴裡嘟囔著「快死了」,一邊說著一邊進神社參拜,可他們看上去又非常健康。經過一番推理,他們才知道,那倆人不過是打算用麻糬粘香火錢的小偷罷了,所謂的「快死了」不過是用來形容他們的經濟狀況而已(比如我們口語中的「窮死了」)。 告別的那一天終究還是到來了,大家為瑪婭舉辦歡送會,並在歡送會當中談論自己名字的意思。對瑪婭心生愛慕的守屋想要跟她一起回南斯拉夫,體驗所謂的「別樣人生」,而瑪婭當然是毫不猶豫的拒絕了。 瑪婭回國後,南斯拉夫的內戰就開打了。守屋想要前往南斯拉夫尋找瑪婭,便跟白河試著推理出瑪婭居住的城市。守屋認為瑪婭現在位於危險的戰亂城市裡,便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前去的計畫。最終,如同守屋對瑪婭的感情那樣,對守屋過家家一般的幼稚行徑忍無可忍的太刀洗拿出瑪婭哥哥的來信,表示瑪婭早已被狙擊兵射殺。因為怕守屋真的前往南斯拉夫,比起性格淳樸,可能沒法保守秘密的白河,知道守屋心意的瑪婭只把地址給到了太刀洗。故事的尾聲,是守屋跟太刀洗一同把她哥哥從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寄來的繡球花髮夾埋進了墓園。此時萬念俱灰的守屋,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命運的無力感」。連最堅強的瑪婭都無力做出什麼改變,自己一介平凡的書生,又能做到些什麼呢?
有關作者
《再見!妖精》是著名推理小說作家米澤穗信(也就是《冰菓》的作者)的出道作。 類型(推理)小說家的人生總是慘淡的。米澤自打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嘗試寫作,中學的時候有了想寫的東西,憋了五、六個故事,在進大學後,餓死畢業之前寫出來,還好得以觸及到成書發表的地板。隨後他開始了漫長的職業生活——抽煙喝酒、老婆孩子熱炕頭…… 賭上人生的虛構故事,能養活自己、卻永遠得不到更廣泛的認同。米澤埋藏在小說情節中的想法,根本傳達不到別人的耳朵裡。明明已經足夠努力了,卻還是下九流。因為大家都覺得類型小說這種東西,如西班牙公主一樣,不配擁有名為「心」的自我表達。 “我只要看看情節就可以了嘛”、“沒有密室有什麼好看的”、“本格這麼爛還好意思寫出來”…… 如果在所處的類型(推理小說界)中不夠規範、不夠優秀的話,是理應承受這些責難的吧。因為類型小說,理應除了類型之外,什麼都沒有。然而仍然存在著「超類型」的類型小說。在作家如廢墟一般居所中,向著世界直接說出自己的所想,再賦予這想法一個虛構故事的做法,筆者認為足夠能夠得上所謂的「純文學」了。 所以,如果對這樣的作品,加以類型內的非難,私認為是一種苛責。如同著名「超類型」小說《獻給虛無的供物》裡所說:“對於此類在名為「推理」的大船上安穩睡覺而見死不救的讀者,我很想知道你們的感想。 ” 近些年這樣的「超類型」小說中,對筆者很有觸動的主要有三本:這本《再見妖精》、佐藤友哉的《聖誕節的恐怖分子》和西尾維新的《少女不十分》。而其中,表達上最深刻、最具衝擊力的當然是《再見妖精》。因為米澤穗信其人的小說中,幾乎每一本都有某種程度上的自我書寫性,不過在這本中體現得特別直白而已。也因為這本書的主題較其他兩本來說,更加著重筆墨來描寫了有關荒謬的、沉重的青春主題故事。 然而,即使是米澤穗信的技巧,也是無法駕馭這樣的主題的吧。如果以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來對照,那麼《再見妖精》只是到了《悲愴》的程度,即由於表達內容的不同,原有形式已經不能承載這樣的內容。這種違和,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完成度,使得完成了的作品粗糙簡陋而模棱兩可。因為對米澤穗信來說,本格、甚至日常推理的形式,始終還是太狹窄了。 是的,《再見妖精》之前的《愚者的片尾》(「古典部系列」第二部)中,米澤已經表達了對「新本格」的態度——綾辻行人式的驚天詭計,並不是「真實」的,並不是「使人幸福」和“我”所追求的真相,而只是戲作的智術而已。對於米澤式的人物來說,早已愛上了世界、愛上了醜陋的“我”,明明更正確的“我”,卻被拉下舞台,一定不是世界的錯。一切錯誤,都是因為我那無法選擇的降生(《瓶頸》)、因為我是個被土地束縛住的悲慘的日本農民(「古典部系列」中的千反田和此作中的文原)、因為我只是個資料收集器(「古典部系列」中的福部和本作的文原)…… 而正如他在本作中做出的努力宣言“要直白地說出自己的苦澀,寧可粗野和未完成,也要直球胜負地傳達”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希望米澤能像貝多芬一樣,在晚期發明新的形式和技巧,然後用更有力度、更加粗野、更加鋒利的文字譜寫出更為獨立與強勁的作品吧。
全書評析
《再見!妖精》作為一本日常推理小說,推理程度從簡單到難,也從跟角色本身的無關緊要到關係密切。對於能夠提出正確解答的人,對日本文化也要有一定的了解。然而,要接受一個高三學生每日盡全力學習南斯拉夫的地理跟歷史,之後還可以考上大學,以及一個在南斯拉夫長大的外國人可以用流利的日語跟日本人談笑風生,情節似乎天馬行空了點。 全書無一處不洋溢著青春年華特有的氣息:青澀、懵懂、嬉笑怒罵、悲歡離合……而也正是這些顯著的符號化特徵與推理相結合,加劇了故事結局的悲劇性與虛無性。早就知道少女的逝去無可挽回,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五族共和」,早就知道守屋對瑪婭的離去無能為力,早就知道這個小圈子會分崩離析,早就知道文化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早就知道和平中的人們不能干涉已成蕪城的他鄉、卻要對其負責和悔疚…… 一切不過是——「屆かない戀」。 瑪婭對於守屋而言,只不過是人生的過客而已,好比其對日本文化的各種誤解,守屋對她的感情,好似也是那麼的荒誕和無力。 果真如此嗎? 比起很多的同齡人,守屋其實做到了他們沒有做到的一步,即對瑪婭表白,甚至說出了「請帶我回娘家南斯拉夫」這樣的「愛情宣言」。而比起那些被人稱讚的「勇敢者」,之所以大多讀者會認為他的話如此蒼白無力,一邊倒向負面評價的原因是,他的表白失敗了,這就使得他滿腔的熱血成為了滿地的雞毛。他最終也沒能去往異國他鄉,與心儀之人終成眷屬。即便如此,在太刀洗公佈真相之前,筆者認為他試圖靠近瑪婭而所付出努力的精神依然是值得被稱讚的,可惜最終所有努力付諸一紙空文。沒有任何回報的努力,正如對「姿勢正確的射偏與姿勢不正的命中」這一命題的博弈那樣,人們會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甚至辜負了成就其他事情的可能性,而這恰恰忽略了其所曾付出過的努力。是啊,比起那些盡力而為卻落得個功敗垂成下場的人,人們總是把讚許的目光投向那些不問出處的成功者,從而衍生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表白了就能有情人終成眷屬”之流的假象。 通往人生巔峰的道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評判一個人的依據,真的僅止於此了嗎? 比起浮誇的「心靈雞湯」,亦或是人云亦云,不絕於耳的普世價值宣傳詞,這樣對真實的生活,殘酷的現實的反都合主義作品,才更容易深入人心,引發人們對自身處境的切實思考,獲得促進「知行合一」的有效反思。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于心。 90年代初的日本深陷經融危機; 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困於戰火; 90年代初的中國剛歷經學潮鎮壓…… 救贖這種東西,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這個國家,並不存在。 深深打上米澤穗信標籤的,是只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青春文學。 告白了就好了嗎? 直接說出來就好了嗎? 在被問到「你能去南斯拉夫幹什麼」的時候,對著少女說「我喜歡你」,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不能。 但即便是這樣,即便是背負上「在人家墓前放紅白豆包」一般的罵名,即便少女執意回國,即便迎來的是死亡的結局—— 我們也要直白地說出自己的苦澀,寧可粗野和未完成,也要直球胜負地傳達。 這就是米澤穗信用悲悼劇的形式向這個殘酷的世界發出的最後一句怒吼。
“人能忘記殺父之仇,卻忘不了被搶的錢。”
“就是偷這種東西,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竊·格瓦拉
瑪婭曾對守屋說過,自己遊歷四方的原因,就是為了成為偉大的政治家,一統南斯拉夫,創造出屬於人民的第七種文化。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地亞作為當時六個加盟共和國中最富庶的,他們當然希望早日獨立,擺脫分蛋糕給其餘國家的現狀,即便他們曾經是奮斗在同一戰線的親兄弟。 沒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連生存都難以為繼的時候,竊·格瓦拉等眾多犯事者對自己人動手的行徑都會變得習以為常。小到人民,大到國家,這條法則都能通用。 於是乎這就不可避免地創生了兩種思潮:民主與專制。對應文中的觀點即是:「姿勢正確的射偏與姿勢不正的命中」。當一個人快要餓死,一個國家快要淪陷的時候,難道還要考慮接下來維持生存的方式正確與否?抗日游擊隊在打小鬼子的時候還要「正面剛」?這也是某些西方道德綁架方式的其中一種了。 與其說作者在針砭兩種立場的利弊,倒不如說他在用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吻嘲諷了某些大國憑藉軍事和經濟實力,強行干涉、控制小國、弱國的內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區稱霸的政策和行為,以及對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表達了深深的同情。 但這並非僅僅諷刺了西方民主國家,對於作者自身「日本」的立場而言,他也表達了人民深受各種言論的鼓吹,煽動,從而無法擁有一個對世界格局的正確認知的無奈:站在民主國家對立面的「共產主義」就毫無瑕疵可言了嗎?非也。 當瑪婭天真的說出要民主大同,世界大同的時候,當瑪婭竭力地在筆記本上記下那形同虛設的邏輯知識的時候,當瑪婭懷著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準備回國的時候,是什麼引導了她?那就是「共產主義」。從南斯拉夫與前蘇聯解體的結果來看,無論瑪婭回國后會不會死去,很顯然這都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是的,我們不能憑藉一個結局,就去草率的定義「盲目的愛國最終害死了自己」,愛國之心沒有高低貴賤,沒有盲目與智慧之分,但主義有:在共產主義的領導下,愛國者們憑藉一腔熱血揭竿而起,然後敗給了現實:殘酷的利益矛盾驅使他們內鬥,兩敗俱傷,然後被西方資本主義拾了牙慧。所以這個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被兩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也直接導致了該小說無法在兩種價值觀為主流的土地上獲得出版發行的機會。 人能忘記殺父之仇,因為痛不在己;忘不了被搶的錢,因為對自己直接造成了影響。但無論如何,在時代與大環境的綜合作用下,有的事物就是被注定好了的,作為這個龐大機器上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我們實在是難以去停止什麼,難以去改變什麼,比如瑪婭的回歸,比如被炸毀的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比如時下戰火紛飛的敘利亞。但我們能夠從中收穫一份人性的美好与反思:對和平與幸福生活的理想與追求。一個瑪婭倒下了,還會有千千萬萬個更具智慧的瑪婭站起來。「共產主義」潮流下前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解體,與這種前仆後繼不斷逡尋美好生活的價值觀並不矛盾,我們所追求的,是停止這種無謂的犧牲循環,用更加科學,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來爭取,並加以維繫我們現有的和平。這就是你與我,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在不遠的將來必須踐行的使命。 “沒有滴水,哪來江海?”
結語
很多故事都會有這樣的開頭某年某月某日,某男某女在某地相遇……這本《再見,妖精》也是如此但這是不一樣的相逢我也曾是高中生我也曾期待命運的邂逅當然,故事主人公所經歷的是不一樣的邂逅雨天、橋對面、異邦女孩饒有趣味的交談有意義的旅行心中的夢想還有小小的萌動異邦的不解與好奇構成日常之謎民俗、文字技巧、還有完全陌生的異國語言平靜的相逢恬然的相知旅遊、討論、或其他學習日語、學習文化仍然懷抱夢想形成新的文化為此走遍天涯可惜世界不如人意無力阻止分崩離析離別時大家還一起歸去時已各自分離為了夢想而出發為了挽救現實而回家當然,離別會傷感而故事最後的轉折更讓人心碎這就是青春嗎萌動的情意還未開始就如此殘酷地終結如同彈奏一曲中途弦斷彈的人無法繼續聽的人卻已逝去無法挽回又或是難以言喻再見,妖精再見,青春
后记
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壞不壞?壞!咱們的共產主義完不完美?不完美!在這兩種主義的綜合作用下,無數鮮活的生命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甚至還沒有過自由思考的機會。很高興有一天筆者也能把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表達出來,因為同和君作為一名愛國者,一路上遇到過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在一次次面對著良知上的選擇。絕大多數人的評價都是非黑即白的,沒有深度思考過現今的一切的實際狀況是個什麼樣子的。當參與愛國遊行被扣上「叛國」的帽子的時候,筆者也似乎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時那些被批鬥得頭破血流的知識分子內心的痛苦與絕望。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堅定了自己的道路,力求獨立思考,脫離現有的「舒適圈」,去海外的網站了解更多被掩埋的真相,再加以分析與思考。 陳sir曾經跟我說過,與其思考一種思想是怎麼樣的,不如去思考它是怎麼來的。常常聽一些權威團體說某些人在搞分裂,但在我看來,即使這些人真的存在,也不會是那些支持並參與的人,亦不會是那些激進地對他人作攻擊、挑釁、侮辱等等行為的人。這兩種人,實際上都是受害者。既然有受害者。那通常都會有加害者,那麼加害者是誰?至少反正不是剛才說的那兩種人。另外,基本上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才是站在真相和良知那一面的,至少筆者仍未見過有人會發自內心地否定過自己這方面,假如一定要以「客觀存在」作為條件而必須可以套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那對於這些「事情」而言其實是有點不公平的。那麼有趣的地方是,到底對與錯、真相或良知到底是什麼,這似乎已經未必就是些那麼清晰明確的東西了。 「命運無力感」往往是公認的這個體制確實有問題,包括唯權勢和物質至上,導致人與人之間差異太大,尤其使大部分沒有資源的人就算作再多的努力也得不到有成正比的回報,甚至影響了他們自身預期的生活質量,這當然會生產無窮無盡和反復循環的仇恨。對於這樣現狀的憤怒、無奈,無力,一旦有了這些感覺之後,到底是繼續燃燒這種憤怒、甚或是嘗試一鼓作氣地捨身取義、還是其他?筆者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目前那些暫以「命運無力感」自居的人確實大有人在,而與此同時,相信在我們大家的身邊也有很多已有此觸覺而不斷嘗試尋求突破和改變的人,包括早前突然被打壓的勞工NGO負責人。那麼,在已是如此的現實當前,我們到頭來要選擇如前者般接受那個所謂的「命運」,還是加入如後者般用努力和耕耘而求變,還是兩者都不選而另起爐灶?這些所有的選擇都是需要尊重的,前提是既然已有此觸覺,那麼我們先要致力讓他們在為自己作選擇和決定之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