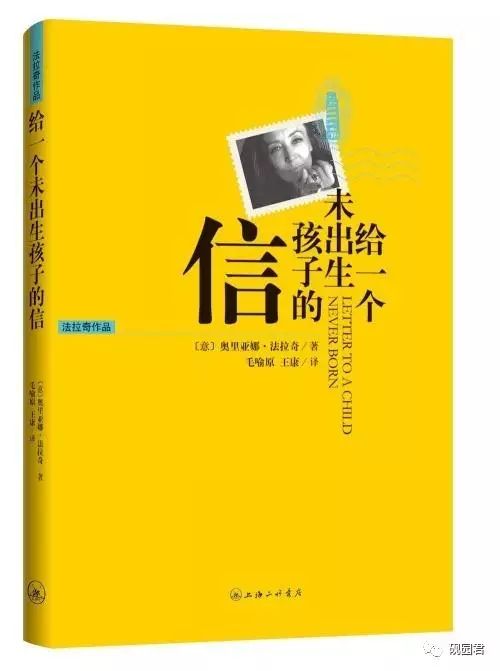
奥丽亚娜·法拉奇这个意大利女记者兼作家是以1980 年8 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为国人所知晓。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访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帕纳古里斯。她没有料到,这个既是疯子又是天才,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男人后来竟然成为她的爱人。1975年,她怀孕了,那一年,她已经46岁了。这或许是一个女人最后的受孕机会。但是,当他知道了她怀孕的消息,从远方打来电话,先是报以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他回来后,在一次争吵中,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孩子流产了。1976年5月1日,一次车祸夺走了他年仅37岁的生命。正是跟帕纳古里斯的爱情以及对他们未能出生孩子的缅怀,让法拉奇创作了一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从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查阅过她的生平,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刚毅、坚毅、无所畏惧的女性,她的作品可以想象应该也是处处体现这种风格吧。但从这本书中,我分明是看到了一个儿女情长、柔情似水,一个对生与死充满了怀疑与痛苦的法拉奇。书中借一个未婚年轻母亲和自己腹中胎儿的对话,告诉孩子她眼中的世界,诉说着自己的爱和恨,温暖而又不失尖锐。虽经受着生理的痛苦、精神的折磨,但她却从与孩子的对话中汲取着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当然这其中还有她对没有出生孩子缠绵悱恻的爱、充满柔情的猜想。

这本带着鲜明时代特色和法拉奇本人明显烙印的书,从写作手法来看是纪实风格和小说想象力自然天成的融合。整部作品始终沉浸在浓烈的感情里,随处可见缠绵的诗意、深沉的思考,比如母亲对肚子里的孩子说:“我希望你具有上帝的特征,其次具有母亲的秉性,最后具有民族的特点。”法拉奇将她个人的几段生活经历伪装成寓言的形式:一个热爱木兰花的女孩,一个爱吃巧克力的孩子,一个相信明天会更美好的小姑娘三个寓言故事,读来朴素平凡,却意味深长地向未出生的孩子讲述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和疯狂,向读者表达了她个人对爱情、金钱和所谓社会公正的理解。
本书尽管没有曲折的剧情,但涉及面却甚广,透露出作者对生命与死亡、富裕与贫穷、工作与权利、伦理与道德、义务与责任的思考。阅读它,更像是在作一种精神的游历,让我体会到她那惊人的理性。追随着她的独语,像“生活就是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的欢乐时刻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爱情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我们彷佛感受到了她坚定的人生信念及她所达到的思想深度。
“怀疑”的主题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该书的自传性质。她的结论是尽管死亡之后便是虚无,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事实,这种认识使人得以对人类的命运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出她作为精神世界的“异乡人”对生命的思考和怀疑。
看完这本书,其实对我最大的触动其实不仅仅是作者深刻的思考,而是我隐约感受到的所谓“伟大的女性”的枷锁对受者的伤害。我们关注伟大的女性,更多的只能看得到她们无所畏惧,让男性自愧不如的刚强的一面,但我更认为一个女性的伟大是两面的,既包括强势,也包括女性特有的细腻思觉的淋漓展现。女性主义者大部分都认为希拉里是一个伟大的角色,因为她做到了很多男性都做不到的地位。请原谅我,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很多女性主义者都认为要想提高女性的地位就必须证明女性也能做男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男性的尊重和认同。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出现“伟大”这个词吗?因为女性所尊崇的“伟大”,男性轻而易举就能做到了,从这个方面说,女性永远也不能追得上男性所取得的成功与地位。而我所认为的女性要想正真的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人,就必须要从男性很难做到而女性可以做到的方面去努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无可取代,正因为无可取代才成就伟大。而女性最难以取代的就是细腻的思考和怜悯的关怀,当女性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细腻的思想光芒,以照耀和软化男性刻板钢化的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守思维;当女性可以无限扩张怜悯的爱心,给予地球上的弱者以希望和关怀的微笑,我想这样的女性才可称之为“伟大的女性”,因为她们真真正正是男性所无法取代的。












